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:在文明对话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,以”两个结合”重塑学术主体性,为人类文明提供新可能。
在全球化遭遇逆流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,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,不仅关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,更是关乎文明主体性的重建。这一历史性工程需要我们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窠臼,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,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新范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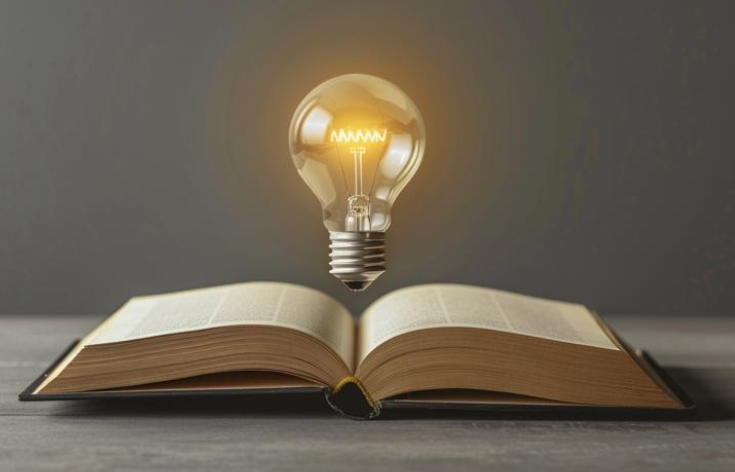
一、知识体系的文明属性与当代困境
现代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。自启蒙运动以来,西方通过将地方性知识普遍化,建立起一套看似”价值中立”实则暗含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。这种知识霸权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:从马克斯·韦伯的”新教伦理”到福山的”历史终结论”,西方学者不断将特定文明经验上升为普世规律。
这种知识殖民的直接后果是学术话语的”双重异化”:一方面,非西方学者被迫通过西方概念框架理解自身文明;另一方面,西方学界也因缺乏真正的文明对话而陷入理论内卷。正如法国学者于连所指出的,当代西方哲学已陷入”自我重复的怪圈”,亟需来自中国思想的”外部视角”。
中国知识界的特殊困境在于,我们同时面临着前现代、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挑战。既要完成知识现代化的未竟事业,又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的覆辙;既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,又要保持文化主体性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走出一条新路。
二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突破
青年马克思提出的”一门科学”理想,为我们破解知识碎片化提供了方法论钥匙。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,马克思预见性地指出:”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,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:这将是一门科学。”这一洞见打破了自然与社会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,为知识体系的整体性重构奠定了哲学基础。
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于,它通过”两个结合”实现了认识论的革命性突破:
-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,打破了理论与实践的机械二分;
-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,弥合了现代知识与传统智慧的断层。
以”矛盾论”为例,毛泽东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,更激活了《易经》”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思维传统,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。这种创造性转化证明,真正的知识自主性必然建立在对多元文明资源的融会贯通之上。
三、文明互鉴中的知识创新路径
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建立”三维一体”的创新框架:
1. 本体论维度:重建文明坐标系
- 开发”中国性”概念工具箱:如”天下体系””和而不同””知行合一”等传统理念的现代阐释
- 建立文明比较方法论:于连的”迂回策略”、张隆溪的”道与逻各斯”对话模式
- 发展跨文明解释学:钱穆”温情与敬意”的史学态度在当代的创造性发展
2. 方法论维度:打破学科壁垒
- 创建问题导向的”超学科”研究范式:如”中国式现代化”研究需整合经济学、政治学、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
- 发展”体用不二”的学术路径:费孝通”文化自觉”理论的当代拓展
- 构建知识生产的”双循环”机制: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动态平衡
3. 实践论维度:扎根中国大地
- 建立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反馈机制: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等重大实践的学理提升
- 开发传统智慧的现代治理资源:”礼治”与”法治”结合的基层治理创新
- 构建自主评价体系:突破SSCI、A&HCI等西方指标依赖
四、知识生产的制度创新
实现知识自主性需要深化学术体制改革:
- 话语转换机制:建立中国术语的国际表达体系,如”小康社会”译为”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”的范式意义
- 人才培养模式:打破文理分科的局限,培育”通儒型”学者
- 学术评价标准:创建兼顾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的多元评价矩阵
- 知识传播网络:建设自主可控的国际学术发表平台
历史表明,真正的知识创新往往发生在文明交汇处。盛唐时期的长安、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、启蒙运动时期的巴黎,都因汇聚多元文明精华而成为知识生产的中心。当代中国正处于类似的文明交汇点,这为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机遇。
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层意义,在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。正如朱熹所言:”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只有扎根中国大地,融通古今中外,我们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蕴含普遍价值的学术成果,为破解全球现代性困境贡献中国智慧。这不仅是学术自立的必然要求,更是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。
发表回复